
張悅然的小說“櫻桃之遠”題目有什么含義
櫻桃之遠的意思她想說那片櫻桃樹,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這種夢想和期待,它們在夢中很近,但在現實中卻遙不可及,夢想和現實之間是有距離的,或者說是有阻隔的。把握驅走心魔,多一些寬容,多一些理解,或許櫻桃樹并不遙遠。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也是一個漫長的取舍和揚棄的過程。打開書,就隨著她輕盈流暢的敘述,走近只有她們這代人才有的成長足跡,仿佛走進另外一個世界。從幼兒園到學校,從小伙伴到同學,從友誼到愛情,在我們這代人眼里,她們這代人似乎就只有這么簡單的經歷,簡單的人際關系,簡單的故事。但在張悅然筆下,在這簡單中展開的卻是一個斑駁陸離的世界,鋪排的是看似偏執(zhí)簡單、實則同樣艱難的心路歷程。正如小說主人公杜宛宛的作畫風格:“線條總是粗而壯碩,它們帶著顫抖的病態(tài),毀壞了畫面的純凈”,所以“只能畫水彩畫或者油畫,用厚厚的顏色蓋住那些心虛而彷徨的線條”,因此“畫總是大塊大塊淤積的顏色,一副不知所云的樣子”。
小說講述了兩個息息相關的女孩——杜宛宛和段小沐從小到大,由敵為友,面對友誼、愛情、生存和死亡的心路歷程。通過她們和紀言、小杰子、唐曉、管道工等人的愛恨情仇,強調了人與人之間的愛,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故事告訴我們,由苦難到平靜、由惡到善的橋梁是皈依宗教。雖然宗教不能阻止人生悲劇的發(fā)生,但卻可幫助悲劇的生命平靜生存,不會因過度恐懼而心智迷狂,不會因過度憎恨而施暴于人,在逆境中同樣可以去尋找幸福。這樣的思想盡管是有所本依,但我認為已經深深地打上了張悅然個人的印記。這是一代新人對困擾人類靈魂的基本問題艱難思索后得出的答案,這里已經基本上散盡神學的光環(huán),閃爍著的是一種人性的光芒,是一種悲憫的人文情懷。這種情懷,成為了在這個原本是虛空和撲風的世界追求幸福生活的支撐。這種情懷,在當今這個怨怨相報、永無止息的世界,更顯得寬宏大量,猶如大教堂管風琴發(fā)出的質樸渾厚的回音。
張悅然不同于那些少年作家,她所講述的顯然不僅僅是青春放縱、反叛傳統(tǒng),而是在成長的迷惘中,小心翼翼地夢想和求證,思索和感悟。她的小說中,沒有了大多數少年作家作品中那種已經變成了時髦套路的憤世嫉俗,沒有了那種貧嘴饒舌和不著邊際的喧囂浮躁,沒有了那種僅僅在字面的意義上玩弄文字的小技巧——那其實還是一種學生腔調,而這一切,是與她思想的深度分不開的。她的思考,總使我感到超出了她的年齡,涉及到了人類生存的許多基本問題,而這些問題,盡管先賢圣哲也不可能給出一個標準答案,但思想的觸角,只要伸展到這個層次,文學,也就貼近了本質。
張悅然耽于幻想的稟賦與憂傷的氣質,使她的小說浪漫而神秘,婉約而典雅。她感官敏銳,多才多藝,在諸多領域嘗試探索,并因之使自己的青春斑駁絢爛。她輕靈精巧地捕捉這個時代賦予的每一個有價值的信息符號,而后完美細致地將之整合在自己的小說中。在故事的框架上,我們可以看到西方藝術電影、港臺言情小說、世界經典童話等的影響。在小說形象和場景上,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動漫的清峻脫俗,簡約純粹;可以看到西方油畫濃烈的色彩與雅靜的光暈;時尚服飾的新潮的樸素與自由的品位;芭蕾舞優(yōu)雅的造型和哥特式建筑驚悚的矗立。在小說語言上,她有流行歌曲的貼近和煽情,詩歌的意境和簡潔,電影經典對白悠長的意蘊和廣闊的心靈空間。這代青少年所接觸的所有有關的文化形式,基本被她照單全收,成為她的龐雜的資源,然后在這共享性的資源上,經過個性稟賦的熔爐,熔鑄出閃爍著個性光彩的藝術特征。
應該說,張悅然是幸運的,是勤奮的,她有了與其年齡并不相稱的寫作才華:超凡的感覺,卓然的思維,對結構和文字的駕馭能力,而這正隨著她的成長而日益枝繁葉茂。她對文學創(chuàng)作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成就了這些點點滴滴的收獲。讀完《櫻桃之遠》,我就有這種感覺,而且同作者一樣,不時也在品味這種收獲帶來的愉悅。作者對于事物的感覺是纖細的,敏銳的,帶有她那個年齡段的一種深入和執(zhí)著。生活中一切事物、現象,都是引發(fā)她產生感覺產生聯想的觸點。不用說書中的秋千、教堂、櫻桃——這是一種特有的情結,成為書中人物固有的一部分。看見的,聽到的,想起的,她都可以對其進行感覺刻畫和心理剖析,這也許同大多數人喜歡從閱讀中進行品味思考的接受習慣并不一樣。
但的確是對事物的感覺,對人物心理的剖析,傾注了作者大量的心血和筆墨。在這方面,她細致描繪,悉心經營,有的甚至達到了鋪張的程度。愛情和友情是需要心與心的互相感知的,穿插其間的各種猜忌和誤會,糾纏與逃避,背叛與反抗,以及因愛而使人物性格發(fā)生的轉變,個性的張揚凸顯等都被作者一筆一筆地如雕刻刀一般削開,剝啟,顯示出其真實透徹的一面,無需再掩卷長思,雖然作者也事先埋下一點伏筆,設置些懸念,但在這快速閱讀的時代,這一切都不足以形成閱讀的障礙。而在手段上,不斷變換敘述角度是最直接的方法,作品多是以杜宛宛第一人稱傾訴,間或以段小沐的角度把段的心理感知表白出來,加上作者巧妙地把兩位女主人公精心設置成心存感應互有你我的關系,為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提供了更廣闊的敘述空間。利用看紀言的日記,閱讀管道工的寫作也都可以更快捷地了解其心理行蹤。這是張悅然敏銳的感覺,她善于利用感覺,描述和玩味感覺,在《葵花走失在1890》里是在《櫻桃之遠》中她依然發(fā)揮著這種非同一般的感覺,收獲著描繪感覺所帶來的愉悅。象她這樣的年輕人是善于發(fā)現和利用自己的優(yōu)勢的。
讀罷小說,和作者先前的小說集《葵花走失在1890》相比,我驚嘆于張悅然的成長,驚嘆于她的進步。這種進步不僅僅在于她的才華,她的結構設置和語言駕馭,還有她對生命和生活的解讀,對于人性的思索。或許這正是作者在成長過程中的一點收獲,一絲品味。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張悅然的寫作道路上,還會有更多的收獲,讓讀者和她一同去品味。我也有她的書《誓鳥》。。也可以去看看
阿朱之死 小說片段
眼見天色漸漸黑了下來,阿朱伏在他懷中,已然沉沉睡熟。蕭峰拿出三錢銀子,給了那家農家,請他騰了一間空房出來,抱著阿朱,放在床上,給她蓋上了被,放下了帳子,坐在那農家堂上閉目養(yǎng)神,不久便沉沉睡去。
小睡了兩個多時辰,開門出來,只見新月已斜掛樹頂,西北角上卻烏云漸漸聚集,看來這一晚多半會有大雷雨。
蕭峰披上長袍,向青石橋走去。行出五里許,到了河邊,只見月亮的影子倒映河中,西邊半天已聚滿了黑云,偶爾黑云中射出一兩下閃電,照得四野一片明亮。閃電過去,反而更顯得黑沉沉地。遠處墳地中磷火抖動,在草間滾來滾去。
蕭峰越走越快,不多時已到了青石橋頭,一瞧北斗方位,見時刻尚早,不過二更時分,心道:“為了要報大仇,我竟這般沉不住氣,居然早到了一個更次。”他一生中與人約會以性命相拚,也不知有過多少次,對方武功聲勢比之段正淳更強的也著實不少,今晚卻異乎尋常的心中不安,少了以往那一股一往無前、決一死戰(zhàn)的豪氣。
立在橋邊,眼看河水在橋下緩緩流過,心道:“是了,以往我獨來獨往,無牽無掛,今晚我心中卻多了一個阿朱。嘿,這真叫做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了。”想到這里,不由得心底平添了幾分柔情,嘴邊露出一絲微笑,又想:“若是阿朱陪著我站在這里,那可有多好。”
他知段正淳的武功和自己差得太遠,今晚的拚斗不須掛懷勝負,眼見約會的時刻未至,便坐在橋邊樹下凝神吐納,漸漸的靈臺中一片空明,更無雜念。
驀地里電光一閃,轟隆隆一聲大響,一個霹靂從云堆里打了下來。蕭峰睜開眼來,心道:“轉眼大雨便至,快三更了罷?”
便在此時,見通向小鏡湖的路上一人緩步走來,寬袍緩帶,正是段正淳。
他走到蕭峰前面,深深一揖,說道:“喬幫主見召,不知有何見教?”
蕭峰微微側頭,斜睨著他,一股怒火猛地在胸中燒將上來,說道:“段王爺,我約你來此的用意,難道你竟然不知么?”
段正淳嘆了口氣,說道:“你是為了當年雁門關外之事,我誤聽好人之言,受人播弄,傷了令堂的性命,累得令尊自盡身亡,實是大錯。”
蕭峰森然道:“你何以又去害我義父喬三槐夫婦,害死我恩師玄苦大師?”
段正淳緩緩搖頭,凄然道:“我只盼能遮掩此事,豈知越陷越深,終至難以自拔。”
蕭峰道:“嘿,你倒是條爽直漢子,你自己了斷,還是須得由我動手。”
段正淳道:“若非喬幫主出手相救,段某今日午間便已命喪小鏡湖畔,多活半日,全出閣下之賜。喬幫主要取在下性命,盡管出手便是。”
這時轟隆隆一聲雷響,黃豆大的雨點忽喇喇的灑將下來。
蕭峰聽他說得豪邁,不禁心中一動,他素喜結交英雄好漢,自從一見段正淳,見他英姿爽颯,便生惺惺相惜之意,倘若是尋常過節(jié),便算是對他本人的重大侮辱,也早一笑了之,相偕去喝上幾十碗烈酒。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豈能就此放過?他舉起一掌,說道:“為人子弟,父母師長的大仇不能不報。你殺我父親、母親、義父、義母、受業(yè)恩師,一共五人,我便擊你五掌。你受我五掌之后,是死是活,前仇一筆勾銷。”
段正淳苦笑道:“一條性命只換一掌,段某遭報未免太輕,深感盛情。”
蕭峰心道:“莫道你大理段氏武功卓絕,只怕蕭峰這掌力你一掌也經受不起。”說道:“如此看掌。”左手一圈,右掌呼的一聲擊了出去。
電光一閃,半空中又是轟隆隆一個霹靂打了下來,雷助掌勢,蕭峰這一拳擊出,真具天地風雷之威,砰的一聲,正擊在段正淳胸口。但見他立足不定,直摔了出去,拍的一聲撞在青石橋欄干上,軟軟的垂著,一動也不動了。
蕭峰一怔:“怎地他不舉掌相迎?又如此不濟?”縱身上前,抓住他后領提了起來,心中一驚,耳中轟隆隆雷聲不絕,大雨潑在他臉上身上,竟無半點知覺,只想:“怎地他變得這么輕了?”
這天午間他出手相救段正淳時,提著他身子為時頗久。武功高強之人,手中重量便有一斤半斤之差,也能立時察覺,但這時蕭峰只覺段正淳的身子斗然間輕了數十斤,心中驀地生出一陣莫名的害怕,全身出了一陣冷汗。
便在此時,閃電又是一亮。蕭峰伸手到段正淳臉上一抓,著手是一堆軟泥,一揉之下,應手而落,電光閃閃之下,他看得清楚,失聲叫:“阿朱,阿朱,原來是你!”
只覺自己四肢百骸再無半點力氣,不由自主跪了下來,抱著阿朱的雙腿。他知適才這一掌使足了全力,武林中一等一英雄好漢若不出掌相迎,也必禁受不起,何況是這個嬌怯怯的小阿朱?這一掌當然打得她肋骨盡斷,五臟震碎,便是薛神醫(yī)在旁即行施救,那也必難以搶回她的性命了。
阿朱斜倚在橋欄干上,身子慢慢滑了下來,跌在蕭峰身上,低聲說道:“大哥,我……我……好生對你不起,你惱我嗎?”
蕭峰大聲道:“我不惱你,我惱我自己,恨我自己。”說著舉起手來,猛擊自己腦袋。
阿朱的左手動了一動,想阻止他不要自擊,但提不起手臂,說道:“大哥,你答允我,永遠永遠,不可損傷自己。”
蕭峰大叫:“你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
阿朱低聲道:“大哥,你解開我衣服,看一看我左肩。”蕭峰和她關山萬里,同行同宿,始終以禮自持,這時聽她叫自己解她衣衫,倒是一怔。阿朱道:“我早就是你的人了,我……我……全身都是你的。你看一看……看一看我左肩,就明白了。”
蕭峰眼中含淚,聽她說話時神智不亂,心中存了萬一的指望,當即左掌抵住她背心,急運真氣,源源輸入她體內,盼能挽救大錯,右手慢慢解開她衣衫,露出她的左肩。
天上長長的一道閃電掠過,蕭峰眼前一亮,只見她肩頭膚光勝雪,卻刺著一個殷紅如血的紅字:“段”。
蕭峰又是驚奇,又是傷心,不敢多看,忙將她衣衫拉好,遮住了肩頭,將她輕輕摟在懷里,問道:“你肩上有個‘段’字,那是什么意思?”
阿朱道:“我爹爹、媽媽將我送給旁人之時,在我肩上刺的,以便留待……留待他日相認。”蕭峰顫聲道:“這‘段’字,這‘段’字……”阿朱道:“今天日間,他們在那阿紫姑娘的肩頭發(fā)見了一個記認,就知道是他們的女兒,你……你……看到那記認嗎?”蕭峰道:“沒有,我不便著。”阿朱道:“她……她肩上刺著的,也是一個紅色的‘段’字,跟我的一模一樣。”
蕭峰登時大悟,顫聲道:“你……你也是他們的女兒?”
阿朱道:“本來我不知道,看到阿紫肩頭刺的字才知。她還有一個金鎖片,跟我那個金鎖片,也是一樣的,上面也鑄著十二個字。她的字是:‘湖邊竹,盈盈綠,報平安,多喜樂。’我鎖片上的字是:‘天上星,亮晶晶,永燦爛,長安寧。’我……我從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道是好口采,卻原來嵌著我媽媽的名字。我媽媽便是那女子阮……阮星竹。這對鎖片,是我爹爹送給我媽媽的,她生了我姊妹倆,給我們一個人一個,帶在頸里。”
蕭峰道:“我明白啦,我馬上得設法給你治傷,這些事,慢慢再說不遲。”
阿朱道:“不!不!我要跟你說個清楚,再遲得一會,就來不及了。大哥,你得聽我說完。”蕭峰不忍違逆她意思,只得道:“好,我聽你說完,可是你別太費神。”阿朱微微一笑,道:“大哥,你真好,什么事情都就著我,這么寵我,如何得了?”蕭峰道:“以后我更要寵你一百倍,一千倍。”
阿朱微笑道:“夠了,夠了,我不喜歡你待我太好。我無法無天起來,那就沒人管了。大哥,我……我躲在竹屋后面,偷聽爹爹、媽媽,和阿紫妹妹說話。原來我爹爹另外有妻子的,他和媽媽不是正式夫妻,先是生下了我,第二年又生下了我妹妹。后來我爹爹要回大理,我媽媽不放他走,兩人大吵了一場,我媽媽還打了他,爹爹可沒還手。后來……后來……沒有法子,只好分手。我外公家教很嚴,要是知道了這件事,定會殺了我媽媽的。我媽媽不敢把我姊妹帶回家去。只好分送了給人家,但盼日后能夠相認,在我姊妹肩頭都刺了個‘段’字。收養(yǎng)我的人只知道我媽媽姓阮,其實,其實,我是姓段……”
蕭峰心中更增憐惜,低聲道:“苦命的孩子。”
阿朱道:“媽媽將我送給人家的時候,我還只一歲多一點,我當然不認得爹爹,連見了媽的面也不認得。大哥,你也是這樣。那天晚上在杏子林里,我聽人家說你的身世,我心里很難過,因為咱們倆都是一樣的苦命孩子。”
電光不住閃動,霹靂一個接著一個,突然之間,河邊一株大樹給雷打中,喀喇喇的倒將下來。他二人于身外之物全沒注意,雖處天地巨變之際,也如渾然不覺。
阿朱又道:“害死你爹爹媽媽的人,竟是我爹爹,唉,老天爺的安排真待咱們太苦,而且……從馬夫人口中,套問出我爹爹名字來的,便是我自己。我若不是喬裝了白世鏡去騙她,她也決不肯說我爹爹的名字。人家說,冥冥中自有天意,我從來不相信。可是……可是……你說,能不能信呢?”
蕭峰抬起頭來,滿天黑云早將月亮遮得沒一絲光亮,一條長長的閃電過去,照得四野通明,宛似老天爺忽然開了眼一般。
他頹然低頭,心中一片茫然,問道:“你知道段正淳當真是你爹爹,再也不錯么?”
阿朱道:“不會錯的。我聽到我爹爹、媽媽抱住了我妹子痛哭,述說遺棄我姊妹二人的經過。我爹娘都說,此生此世,說什么也要將我尋了回來。他們哪里猜得到,他們親生的女兒便伏在窗外。大哥,適才我假說生病,卻喬裝改扮了你的模樣,去對我爹爹說道,今晚青石橋之約作罷,有什么過節(jié),一筆勾銷,再裝成我爹爹的模樣,來和你相會……好讓你……
好讓你……”說到這里,已是氣若游絲。
蕭峰掌心加運內勁,使阿朱不致脫力,垂淚道:“你為什么不跟我說了?要是我知道他便是你的爹爹……”可是下面的話再也說不下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他事先得知,段正淳便是自己至愛之人的父親,那便該當如何。
阿朱道:“我翻來覆去,思量了很久很久,大哥,我多么想能陪你一輩子,可是那怎么能夠?我能求你不報這五位親人的大仇么?就算我胡里胡涂的求了你,你又答允了,那……
那終究是不成的。”
她聲音愈說愈低,雷聲仍是轟轟不絕,但在蕭峰聽來,阿朱的每一句話,都比震天響雷更是驚心動魄。他揪著自己頭發(fā),說道:“你可以叫你爹爹逃走,不來赴這約會!或者你爹爹是英雄好漢,不肯失約,那你可以喬裝了我的模樣,和你爹爹另訂約會,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在一個遙遠的日子里再行相會。你何必,何必這樣自苦?”
阿朱道:“我要叫你知道,一個人失手害死了別人,可以全非出于本心。你當然不想害我,可是你打了我一掌。我爹爹害死你的父母,也是無意中鑄成了大錯。”
蕭峰一直低頭凝望著她,電光幾下閃爍,只見她眼色中柔情無限。蕭峰心中一動,驀地里體會到阿朱對自己的深情,實出于自己以前的想象之外,心中陡然明白:“段正淳雖是她生身之父,但于她并無養(yǎng)育之恩,至于要自己明白無心之錯可恕,更不必為此而枉自送了性命。”顫聲道:“阿朱,阿朱,你一定另有原因,不是為了救你父親,也不是要我知道那是無心鑄成的大錯,你是為了我!你是為了我!”抱著她身子站了起來。
阿朱臉上露出笑容,見蕭峰終于明白了自己的深意,不自禁的歡喜。她明知自己性命已到盡頭,雖不盼望情郎知道自己隱藏在心底的用意,但他終于知道了……
蕭峰道:“你完全是為了我,阿朱,你說是不是?”阿朱低聲道:“是的。”蕭峰大聲道:為什么?為什么?”阿朱道:“大理段家有六脈神劍,你打死了他們鎮(zhèn)南王,他們豈肯干休?大哥,那《易筋經》上的字,咱們又不識得……”
蕭峰恍然大悟,不由得熱淚盈眶,淚水跟著便直灑了下來。
阿朱道:“我求你一件事,大哥,你肯答允么?”蕭峰道:“別說一件,百件千件也答允你。”阿朱道:“我只有一個親妹子,咱倆自幼兒不得在一起,求你照看于她,我擔心她走入了歧途。”蕭峰強笑道:“等你身子大咱們找了她來跟你團聚。”阿朱輕輕的道:“等我大好了……大哥,我就和你到雁門關外騎馬打獵、牧牛牧羊,你說,我妹子也肯去嗎?”
蕭峰道:“她自然會去的,親姊姊、親姊夫邀她,還不去嗎?”
忽然間忽喇一聲響,青石橋橋洞底下鉆出一個人來,叫道:“羞也不羞?什么親姊姊、親姊夫了?我偏不去。”這人身形嬌小,穿了一身水靠,正是阿紫。
蕭峰失手打了阿朱一掌之后,全副精神都放在她的身上,以他的功夫,本來定可覺察到橋底水中伏得有人,但一來雷聲隆隆,暴雨大作,二來他心神大亂,直到阿紫自行現身,這才發(fā)覺,不由得微微一驚,叫道:“阿紫,阿紫,你快來瞧瞧你姊姊。”
阿紫小嘴一扁,道:“我躲在橋底下,本想瞧你和我爹爹打架,看個熱鬧,哪知你打的竟是我姊姊。兩個人嘮嘮叨叨,情話說個不完,我才不愛聽呢。你們談情說愛那也罷了,怎地拉扯到了我身上?”說著走近身來。
阿朱道:“好妹妹,以后,蕭大哥照看你,你……你也照看他……”
阿紫格格一笑,說道:“這個粗魯難著的蠻子,我才不理他呢。”
蕭峰驀地里覺得懷中的阿朱身子一顫,腦袋垂了下來,一頭秀發(fā)披在他肩上,一動也不動了。蕭峰大驚,大叫:“阿朱,阿朱。”一搭她脈搏,已然停止了跳動。他自己一顆心幾乎也停止了跳動,伸手探她鼻息,也已沒了呼吸。他大叫:“阿朱!
阿朱!”但任憑他再叫千聲萬聲,阿朱再也不能答應他了,急以真力輸入她身體,阿朱始終全不動彈。
阿紫見阿朱氣絕而死,也大吃一驚,不再嬉皮笑臉,怒道:“你打死了我姊姊,你……你打死了我姊姊。”
蕭峰道:“不錯,是我打死了你姊姊,你應該為你姊姊報仇。快,快殺了我罷!”他雙手下垂,放低阿朱的身子,挺出胸膛,叫道:“你快殺了我。”真盼阿紫抽出刀來,插入自己的胸膛,就此一了百了,解脫了自己無窮無盡的痛苦。
小說中《暮光之城》最后的結局是什么
這是第五部的結局,希望是你要的,我這還有全集,如果你需要就告訴我,我發(fā)給你
我的手刺痛。我彎曲它們,然后蜷縮成拳頭,但它繼續(xù)痛苦的刺痛。
不,我不會傷害她——但觸摸她仍是一個錯誤。
感覺就像火一樣——我的喉嚨那燃燒的渴望已經遍布我的全身。
下一次我接近她,我能夠阻止自己再次觸摸她嗎?如果我再一次撫摸她,我能夠制止住嗎?
不能犯更多的錯。就是這樣。品嘗那記憶,愛德華,我冷冷地告訴自己,管好自己的雙手。如此這般,不知何故我強迫自己離開。因為我不能允許自己靠近她,如果我要堅持制造這種錯誤的話。
我深吸一口氣,試圖穩(wěn)定我的思緒。
埃梅特在英語課的建筑物前趕上我。
“Hey,愛德華。”他看上去很好。奇怪的,比之前更好。快樂的。
“Hey,Em”。我看上去也快樂?我猜想,盡管我的思緒很混亂,我感覺得到是這樣。
『找個方式讓你的嘴巴閉上,小孩。羅莎莉要撕裂你的舌頭了。』
我嘆了口氣。“對不起,我留下你去處理。你生我的氣嗎?”
“Naw。羅莎莉會克服它的。反正這是必然會發(fā)生的。”『與愛麗絲看到的未來。』
愛麗絲的影像并不是我這刻要去思考的。我看向前方,我的牙齒緊鎖在一起。
當我尋求著分散注意時,我看見了班切尼在我們面前進入了西班牙文課室。Ah——這便有我送給安吉拉韋伯她的禮物的機會了。
我停了下來,并抓住埃梅特的胳膊。“等一秒。”
『怎麼回事?』
“我知道不該得到的,但你能幫我個忙嗎?”
“什麼事?”他好奇的問。
在我的呼吸之下——我用飛快的速度說話,這樣的話,就算一個人類無論他們的說話多麼響亮都是難以理解的——我向他解釋我想要的。
我這樣做時他茫然地望著我,他的思想如同他的臉一樣空白。
“真的嗎?”我提示。“你愿意幫助我做到這一點嗎?”
這讓他在一分鐘后才作出回應。“為什麼?”
“來吧,埃梅特。為什麼不呢?”
『你是誰,你對我的兄弟做了什麼?』
“不是你常抱怨說學校總是一成不變的嗎?這只是有點不同,不是嗎?把它作為一個實驗——實驗人類的本性。”
在他跌入陷阱之前的其余時間他都在盯著的。“Well,這真是不同的,我會給你你想要的。行了嗎,好吧。”埃梅特吸了口氣,然后聳聳肩。“我會幫你的。”
我向他笑,感覺更熱衷於現在有他在內的我的計劃。羅莎莉是一種痛苦,但我選擇埃梅特這件事將永遠欠她一個人情;沒有人比我有更好的兄弟了。
埃梅特不需實習。我低聲說他行他曾經在我的呼吸,我們走進了課堂。
在我的呼吸聲下我低語的告訴他一次他的路線,在我們走進課室時。
班已坐在我后面的他的座位上,把他的功課聚集在他的手中。
埃梅特和我都坐著,也做了同樣的事情。課堂上還沒有安靜下來;細微的雜音對話將持續(xù),直到Mrs. Goff叫他們專心上課。
她并不心急,最后一堂課是考核測驗
“”埃梅特說,他的音量比平常大——如果他真的只是說給我聽。“你問了安吉拉韋伯了沒有?”
在我后面?zhèn)鞒龅募垙埖纳成陈曉诎嗟慕┯蚕峦回MV梗淖⒁饬ν蝗蛔⒓以谖覀兊膶υ挕?/p>
『安吉拉?他們在談論安吉拉?』
太好的。他對我的話題感興趣。
“沒有,”我說,我慢慢地搖了搖頭,表現出遺憾。
“為什麼不呢?”埃梅特湊合著我。“你是雞嗎?”
我向他扮個鬼臉。“不,我聽說她對其他人感興趣。”
『愛德華庫倫想約安吉拉出去?但是……不。我不喜歡這樣。我不想讓他靠近她。他……不適合她。不……安全。』
我沒有預計他是出於騎士精神,出於保護本能。我還以為嫉妒會行得通的。但也是行得通的。
“你要我告訴你,我可以有效地阻止你嗎?”埃梅特輕蔑,再次湊會著我。“不競爭?”
我瞪著他,但他給我的很有用。“你看,我猜她非常喜歡這個叫班的人。而且我不會試圖說服她。還有其他女孩。”
在我身后的那張椅子的反應如像電動般。
“誰?”埃梅特要求,回到腳本。
“我實驗室的合作夥伴說是一個名叫切尼的家伙。我不確定我是否知道他是誰。〃
我給回他一個微笑。只有高傲的庫倫家可以假裝不知道在這個小小的學校的每個學生。
班的頭部震動的旋轉。『我嗎?超過愛德華庫倫?為什麼她會喜歡我?』
“愛德華”,埃梅特低沉的咕嚕著,滾動他的眼睛看向前面的男孩。
“他在你身后的右邊,”他滿嘴臟話,顯然,人類可以輕松閱讀他的話。
“噢,”我咕嚕著回應。
我在我的座位轉過身,并看了一眼身后的男孩。在這一秒,眼鏡后的黑眼睛被嚇壞了,但他狹窄的肩膀變得僵硬和筆直,被我清晰的貶低評價冒犯了。他的憤怒萌芽并漆黑了他金棕色的皮膚。
“Huh,”我傲慢地回應埃梅特。
『他認為自己比我好。安吉拉并不認為。我會向他展示實力的。』?
完美。
“你不是說她在是考慮與Yorkie跳舞嗎?”埃梅特哼了一聲的問道,正如他鄙視口中所說的男孩的名字多麼笨拙。
“這是顯然是一個組合的決定。”我想要肯定班清楚這一點。“安吉拉害羞。如果B——Well,如果那個小子沒有勇氣約她出去,她也永不會開口問他的。〃
”你喜歡害羞的女孩,〃埃梅特說,回到即興的劇本。『文靜的女孩,就像是……h(huán)mm,我不知道。或者是貝拉史旺?』
我瞪著他。”正是。〃然后我又回到我的表演。”或者安吉拉對於這等待感到疲累。或者我會問她能否和我一起去舞會。〃
『不,你不會,』班想道,弄直了他的椅子。『那麼,如果她比我高那麼多?如果她不介意,然后我也不介意。她是這所學校里最友善的,最聰明的,最漂亮的女孩……而且她要我。』
我很喜歡這個班。他看上去似乎光明正大和善意的。甚至值得得到像安吉拉這樣的好女孩。
我在桌下給埃梅特一個大拇指,在Mrs. Goff站起來向班級里的學生們打招呼時。
『好吧,我承認——這是一種樂趣,』埃梅特心想。
我向自己笑了,為自己能促使一個愛情故事有個完美結局而歡欣。
班將會貫徹我的積極,而安吉拉將得到我的匿名禮物。我的債務償還了。
多麼愚蠢的人類,讓六英寸的身高差別混淆了他們的幸福。
我的成功使我心情愉快。我坐在椅子上再次為我解決了這件事而笑了,然后準備離開。畢竟,貝拉曾在午餐時指出,我從未見過她上體育課時的表現。
邁克的想法是最容易確定的,潺潺的聲音聚集在體育館內。在過去幾周,我對他的心理已經變得太熟悉了。嘆了一口氣,我服從自己的命令去聽他的想法。至少我可以肯定,他非常專注於貝拉。
我只是在從他提出愿意成為她的羽毛球夥伴這個建議時聽他的內心,然而其他合作夥伴貫穿了他的思想。我的笑容漸漸淡去,我咬緊牙關,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殺害邁克紐頓是不容許的選項。
“謝謝,邁克——你不用做到這樣的,你知道。”
“別擔心,我會與你保持距離的。”
他們交換了一個笑容,并閃爍無數意外——總是以某種方式連接到貝拉——通過邁克的頭部閃現。
邁克首先獨自仍戰(zhàn),而貝拉在球場后方猶豫,小心翼翼的緊握自己的球拍,就像那是某類型的武器。然后克拉普教練在旁緩行慢步,并下令邁克讓貝拉參與。
Uh oh,邁克想著貝拉向前移動時嘆了一口氣,在一個尷尬的角度及時握著她的的球拍。
Jennifer Ford向著貝拉的正面打出一個低飛球,自鳴得意的扭曲貝拉的想法。邁克看到貝拉蹣跚的走向它,擺動球拍瞄準她的目標,然后他貿然的嘗試拯救這一截擊。
我憂慮的看著貝拉球拍的軌跡。果然,它擊中那拉緊的球網,然后向她反彈,在它失控的撞擊麥克的胳膊發(fā)出一聲響亮的拍打聲之前猛擊了她的前額。
Ow。Ow。Ungh。這肯定會留下瘀青。
貝拉是揉著她的額頭。當知道她受了傷時,我很難再留在屬於我的位置上。
但如果我在那兒的話我能做些什麼?而且它看上去并不是太過嚴重。我猶豫著,觀看著。如果她打算繼續(xù)再玩,我將會制造一個藉口去將她從課堂拉走。
教練大笑。”抱歉,紐頓。〃『那個女孩的厄運是我看過最惡劣的。不能再使她在其他地方受到這種遭遇了。』
他故意轉身背對著觀賞另一場比賽,以便貝拉能回到她的前旁觀者的角色。
邁克按摩著他的手臂再次思考。他轉過身向著貝拉。“你還好吧?”
”Yeah,你呢?〃貝拉紅著臉羞怯的回答。
“我想我會做得到的。”『不想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像是一個愛哭的人。man,受了傷呀!』
邁克打圈的旋轉著他的手臂,臉部肌肉卻在抽搐。
“我將會留在這兒,”貝拉說,在她的臉上,寫滿著多於痛苦的尷尬和懊惱。
或許邁克已經得到了最壞的情況了。我當然希望是這樣。至少她不會再玩。
她小心的在她背后緊握著她的球拍,她憐憫的眼神張得很大——我用咳嗽來掩飾我的笑聲。多麼有趣?埃梅特會想知道的。
“待會再告訴你,”我喃喃地說。
貝拉沒有再加入到游戲之中。教練無視了她,并讓邁克單獨發(fā)揮。
我最后輕松的通過了這段時間里的考試,Mrs. Goff讓我先走了。當我走過校園時,我密切的聆聽著邁克。他決定面對貝拉,談及關於我的事。
杰西卡咒罵他們的約會。『為什麼?他為什麼要去接她?』
他沒有認識到真正的現象——是她選擇了我。
“所以。”
”所以什麼?〃她想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和庫倫,huh?〃『你和那只怪物。我猜想,如果一個富有的家伙對你來說是很重要……』
他這種有辱人格的假設使我緊咬牙齒。
“這不關你的事,邁克。〃
『防衛(wèi)。這是真的。廢物。』“我不喜歡這樣。”
“你不需要喜歡,”她總結。
『為什麼她沒有看到他像馬戲團的雜耍似的?他們全都像。』這一過程中,他看著她的眼神。著實讓我觀看得發(fā)抖。“他看著你時,就好像你是美味的大餐。”
我卑躬屈膝的等待著她的反應。
她的臉頰變得紅潤,她緊抿著唇瓣就像是為了穩(wěn)住她的呼吸般。突然之間,從她的唇間爆發(fā)出格格大笑。
『她在嘲笑我了。很棒。』
麥克轉過身來,陰沉的思考,并不停地徘徊。
我靠在健身室的外墻上,并試圖組合她的意思。
她怎麼會嘲笑麥克的指控——我開始擔心福克斯的人會變得非常注意這個如此完全的目的。當她知道那是完全正確的推論,她為什麼還會嘲笑這個我有可能會殺死她的暗示呢?這里面有幽默的地方嗎?
她究竟有什麼問題?
她有病態(tài)的幽默感官嗎?她的性格不符合我的想法,但我又怎麼能肯定呢?或許我那個關於輕浮的天使的白日夢在某一方面才是真的,當中她沒有任何一點恐懼感。勇敢——一個字已經說明了一切。
其他人可能會說這是愚蠢的,但我知道她是多麼聰穎的。無論是什麼原因,雖說,這種缺乏恐懼或扭曲的幽默感是不利於她。就是這種異於常人的缺乏,使她常處於危險當中嗎?或者,她會需要我常在她的身旁。
就像我的情緒正在高漲。
如果若我能訓練好我自己,使自己是安全的,那麼我留在她身邊或許是正確的。
當她穿過健身室的門走出來時,她的肩膀變得僵硬,她的牙齒又再咬著她的下唇——焦慮的跡象。但當她的眼眸接觸到我的時,她那僵硬的肩膀便放松下來,然后一個笑意盈盈便在她的臉上擴展。這是一個奇特的安寧表情。她沒有任何猶豫的走到我的右邊,她的體溫便如像浪潮般沖擊著我,唯有制止她如此接近。
“Hi,”她低聲說。
我感覺到這刻是如此幸福,再一次,沒有先例的。
“你好,”我說,然后——因為我的情緒突然變得明亮,使我無法抗拒去取笑她——我補充說:“健身怎麼樣?”
她的笑容搖擺不定。“很好。”
她是一個差勁的說謊者。
”真的嗎?〃我追問——我還在擔心她的額頭。她還痛嗎?——但邁克紐頓的思想太過吵雜,它們打斷了我的注意力。
『我憎恨他。我希望他快去死。我希望他駕駛他那輛閃亮的汽車馬上沖向懸崖。
為什麼他不能滾遠離她?忠於他們的種類——怪胎。
“什麼事?”貝拉詢問。
我的眼睛重新回到她的臉上。她望著邁克向后撤退,然后再次望向我。
“紐頓愈來愈臨近我的神經(能容忍的臨界點)了,”我承認。
她的嘴巴張開,笑容消失。她一定是忘記了我能通過別人的思維看到她多災多難的一小時了,或是希望我沒有利用這能力。
“你不是再次偷聽吧?”
“你的額頭怎樣?”
“你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她從她的牙縫溢出這句說話,接著她轉過身去背對著我然后怒氣沖沖的走近停車場。她的皮膚萌芽著深深的紅潮——她尷尬。
我保持著步調跟著她,希望她的憤怒能快速消散。她通常很快就會原諒我。
“你是那個提出我從沒見過你在健身室的樣子的人,”我解釋。“那讓我很好奇。”
她沒有回答,她的眼眉已連成一線了。
當她看清楚在我停泊車子的地方正被一群男學生阻擋著時,她突然在停車場中停了下來。
我驚訝他們已經有多迅速的入迷在這件事。
『看看那SMG換檔。我從來沒有在一本雜志以外的地方看到過。』?
『漂亮的側架。』?
『當然希望我有六萬美元左右去鋪設周圍。』
這正是為什麼蘿莎莉只是用她的車子出城對她來說會更好。
我彎彎曲曲地通過那些貪欲男孩的人群走到我的車旁。貝拉在一秒的猶豫之后跟著我前進。
“炫耀,”我喃喃地說,她爬入車箱中。
“那是什麼類型的車呢?”她想知道。
“M3。”
她皺起了眉頭。“我不是說賽車和車手。”
“這是寶馬。”我轉動我的眼球,然后集中注意力在不會撞倒任何一個人的情況下把車向后退并駛出車道。
我不得不緊盯著那幾個似乎沒有意愿走出我的路線的男孩。接觸我的目光半秒似乎已經足以說服他們走開。
“你還在生氣?”我問她。她放松了皺著的眉頭。
“無疑是這樣的,”她簡略的回答。
我嘆了口氣。也許我不應該帶到這個話題上。Oh well。我可以設法彌補,我假定。“如果我道歉,你會原諒我嗎?”
她想了一會兒說。“可能會……如果你的意思是,”她堅決地說。“如果你答應不再會這樣做。”
我不會騙她的,但我沒辦法應承這一點。也許,如果我提供她另一個條件交換。
“如果我的意思是,我同意讓你在這個星期六開車?”我內心正在畏縮。
一道深溝突然顯現在她的雙目之間,她考慮著這個新的議價。
“成交,”她思考了一會后回答。
我道歉……我之前從未試圖過因一個目的而迷惑貝拉,但現在看來是個好時機。
當我仍在駕駛遠離學校時,我凝視著她的雙眸深處,我想知道如果我這樣做是對的。我用我最有說服力的語氣說。“那麼我很抱歉,我刺激你。”
她的心跳跳動得比之前更大聲,然后那旋律突然斷奏。
她的眼睛睜大,看上去有點目瞪口呆。
我半微笑。那就像是我做對了似的。我也有點難於從她的雙眸中抽離。相等的目炫。這是我在這條道路的記憶中擁有的一件好事。
“於星期六一大早我將會在你家門前亮相,”我說,完成了這個協定。
她眨著眼睛迅速地搖搖頭,彷佛要將其清除。”Um,〃她說“如果一臺不明來歷的沃爾沃停留在車道上,這會不利於與查理說明情況。”
Ah,她多少還算了解我。“我不打算帶上汽車。”
“如何——”,她開始問。
我打斷了她。如果沒有示范是很難解釋答案的,可是現在差不多沒有時間了。”關於這個你不用擔心。我會在這里的,而且不會帶上車。”
她艇另一邊側著頭,期待一秒像是她會得到更多的,但另一方面,她似乎又改變主意了。
“‘之后’到了嗎?”她問,提醒我今天我們在食堂時未完結的談話,她放過一個困難的問題,只是為了回到另一個更有吸引力的問題上。
“我意想得到,這是‘之后’了,”我不情愿的同意。
我停在她家門前,變得緊張的我試圖想像該如何解釋……撇除會使我的野性非常明顯,撇除會再次嚇到她的。或者這是錯的嗎?為了縮小我的黑暗面?
她等待著,并用與午餐時相同的禮貌來掩蓋她對此非常感興趣。
如果我少一點焦慮,她荒謬的冷靜絕對會使我發(fā)笑。
「而你仍然想知道為何你不能看到我狩獵嗎?」我問。
「嗯,主要是我好奇你的反應,」她說。
「我有嚇怕你嗎?」我肯定她會否認這一點的問道。
「沒有。」
我嘗試不笑出來,但是失敗了。”我嚇怕了你,我很抱歉。〃然后我的笑容在瞬間的幽默后消失了。”只是想知道如果你在那里……當我們狩獵時。〃
”這是不好的嗎?〃
一個心理影像已經太多——貝拉,在虛空的黑暗中是多麼脆弱。
我,失去控制……我嘗試從我的腦海中驅逐它。”極其(不好)。〃
”因為……?〃
我深呼吸了一口氣,在一個時刻,集中我那在燃燒的火渴。感覺它,控制它,證明我的主拳的跨過它。它將不能再控制我——我會使這成為真實的。我對她來說是安全的。
我凝視那天際受歡迎的云彩卻沒有看著它們,期望我能堅信我的決心,若我在橫過她的氣味之中狩獵時,會使事情能有所不同。
”當我們狩獵時……我們會把自己交給我們的本能,〃我告訴她,每一個字在我說出口前都經過深思熟慮。”自我治理會更少。特別是我們的嗅覺感官。當我失去控制時……如果你在我附近……〃
我搖搖頭痛苦的思考著那將會——沒有什麼可以,但什麼就會——然后肯定會發(fā)生。
我的聲音如長釘釘住她的心跳,然后我轉過身來,焦躁不安,閱讀她的眼睛。
貝拉的表情很鎮(zhèn)靜,她的眼神嚴肅。我猜測她的嘴巴略微皺起是在關注些什麼的。關注些什麼呢?她自己的安全?抑或我的痛苦?我繼續(xù)盯著她,試圖把她含糊不清的表情直到肯定事實。
她回瞪我。她的眼睛在一瞬后睜得更大,然后她的瞳孔擴張,盡管那光線沒有改變。
我的呼吸加速,突然安靜的汽車似乎是響起嗡嗡聲,如同下午時在漆黑一片的生物學教室當中。脈搏的流動當今在我們之間再次賽跑,我渴望觸摸她,簡單地說,甚至比我口渴的需求更強。
這撲騰的電力使它感覺上如像我再次有脈動似的。我的身體與它一起高歌。就像我仍是人類。我想要感覺她雙唇針對我的熱度,比世界上任何事物都還要多。這一秒,我拼了命的掙扎終於找到力量,控制住,能夠把我的嘴巴更加接近她的肌膚。
她粗糙的吸了一口氣,只有這樣我才意識到,當我開始呼吸加快時,她已經停止呼吸了。
我閉上我的眼睛,試圖打斷我們之間的聯系。
不要犯更多的錯。
貝拉的存在是并列一千微妙平衡的化學過程,都是那麼容易受到破壞。她肺部的韻律擴張,氧氣在流動,她是生存還是死亡。
戰(zhàn)斗終止,她脆弱的心臟可以被那麼多愚蠢的事故或疾病或……由我停止。
我并不認為我家里的任何一個成員都將能毫不猶豫,如果他或她提供了一個機會重頭再來——如果他或她能夠出售不朽來換取再一次的死亡。我們當中任何人都將為了它而站在火中。燃燒多達數天或數百年,如果有必要的話。
在眾多數我們珍貴的實物當中,不朽是高於一切的位置的。甚至有人類渴望得到這一點,誰在黑暗的地方搜查,那誰就可以給予他們最黑暗的禮物。
不是我們。不是我的家庭。我們愿意用任何東西來交換變回人類。
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曾經好像我現在這樣以一種絕望的方式回顧。
我盯著顯微鏡上的坑和擋風玻璃上的缺陷,像有一些解決辦法隱藏的玻璃當中。電力還沒有消退,我必須集中精力使雙手保持放在方向盤上。
我的右手由當我想觸摸她之前便開始再次無疼痛的刺痛。
“貝拉,我想你應該進去了。”
她第一次服從,不加以爭論的,她從汽車中走出去并在身后關上了車門。她清楚的感到了我所帶來的潛在災害了嗎?
她會被傷害得要離開,如同它傷害我使我要離她而去?唯一的安慰是我很快就會再與她見面。早於她想見我前。我笑了笑,然后把車窗調低,并俯身跟她再次對話——現在非常安全了,伴隨著她的體溫在車箱之外。
她轉過身來看看我想怎樣,好奇地。
仍然好奇,即使今天她已問了我非常多的問題。我自己的好奇心完全不滿意;回答她的問題,今天才發(fā)現我的秘密——我想要從她那里得到什麼,但這只是我自己的猜測。這是不公平的。
“Oh,貝拉?”
“是?”
“明天輪到我了。”
她的前額皺起了皺褶。“輪到你什麼?”
“問問題。”明天,當我們在一個更安全的地方時,被周圍的證人包圍住,我會得到我自己想要的答案。我在腦海里笑了,然后我轉過身去,因為她沒有移動離開。即使她已經在車箱的外面,但在這空間里,我們之間那電力的回音仍在回響。我也想走出去,以陪她走到屋門前為藉口,來繼續(xù)留在她身旁。
不要再犯更多的錯。
在她消失在我身后后,我嘆了口氣。那看起來就像是我時常奔向貝拉,或是從她身邊逃得遠遠的,永不會停留在一個地方。我要找到一些方法,去打好我的基礎,如果我們想要任何時候都維持著和睦的相處的話。
閃爍之光的小說的介紹就聊到這里吧,感謝你花時間閱讀本站內容,更多關于張悅然的小說“櫻桃之遠”題目有什么含義、閃爍之光的小說的信息別忘了在本站進行查找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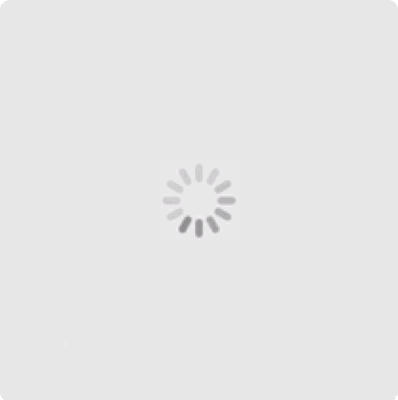
 下載咪嚕游戲盒
下載咪嚕游戲盒